
作者:张 力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0-01-23 浏览次数: 8092次
【摘要】清代前期山西吕梁山区的荒地问题是清初战乱、灾害以及赋役负担下综合层累的结果。虽经豁免与调整,荒地问题仍以各种方式残存,对地方社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一方面,荒地亡丁的除豁使里甲体系进行了重组,但除豁与垦复中的弊病使里甲赋役体系的重建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在垦荒压力下,一些地方逐渐形成本户和佃户县际互换的垦种模式,相沿数代后造成世佃问题。与此同时,大量荒地仍未开垦,且不断有新荒地产生。在荒地钱粮代纳摊赔的影响下,里甲及户族内部也呈现分离倾向。雍正时期石楼县世佃入籍和里甲合理摊派的一系列调整,在制度和事实上重新确立了人口与土地的结合。这些围绕荒地而产生的问题与调整,反映了北方土地贫瘠地区趋于分散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
【关键词】山西省;清代前期;荒地问题;世佃;社会结构
动态来看,荒地问题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土地由熟转荒;其二,荒地无法开垦而持续存在;其三,土地由荒转熟。这三个方面可看做是土地荒熟变动的一个周期,每一阶段对地方社会产生不同影响。荒地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荒地垦复,并被重新纳入赋役体系。这也是明清赋役原额主义下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待荒地的一般态度。因此,以往关于荒地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荒地问题的第三个方面,即垦荒政策、过程及其影响展开。在一些社会经济史和灾荒史研究中,也注意到土地荒熟变动引起的土地兼并与分散,或租佃雇佣关系的变化等问题。然而,土地的荒熟变动并非一蹴而就。在前后相继的周期变动中,新旧荒地经常交替出现,而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应对荒地问题上也有很强的滞后性。由此,荒地问题具有明显的层累性和持续性。在土地荒熟变动频繁地区,荒地问题的出现及相应调整对区域社会产生很大影响。那么荒地问题如何形成演化,对区域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需要我们在动态中进行把握。
在对江南地区的研究中,滨岛敦俊提出了明代中叶的商业化与土地内涵式开发之间的联系。虽然他认为其可能并非完全对应关系,但基本逻辑是,内涵式的荒地开垦表明了土地开发的饱和,由此导致了区域商业化的发展。然而,明代中期以后的荒地问题有更为复杂的形成机制。谢湜的研究揭示了明清江南地区荒地问题与赋役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荒地主要是由赋役改革造成的人为抛荒,开荒很大程度上也是赋役改革的结果。由此对滨岛敦俊的推论提出质疑,并进一步讨论了由荒地问题引发的赋役调整与“异乡甲”的兴废等社会变动。关于北方地区的荒地问题,安介生通过对明代山西自然灾害和人口变动的研究,提出了“田地陷阱”的概念,以解释传统社会大量农民逃避承种土地的问题。“田地陷阱”是荒地问题形成的重要一环,显示了灾害频发、土地相对贫瘠地区荒地问题的不同特征。李大海关于清代陕西黄龙山区匪患与垦荒的考察,揭示了垦荒进程与重建和恢复统治秩序的关系,从区域社会角度提出了与鼓励垦荒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这种“人地关系”模式不同的地方开发解释。
以上研究为我们考察荒地问题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对于清代前期的北方地区来说,清初战乱与频繁的灾害是荒地产生的基础,其规模、形成机制与明代后期及江南地区有很大不同。尤其在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大规模的荒地出现及其后垦荒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对区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山西吕梁山区在清初以后的恢复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农户逃亡异乡与充当佃佣是当地农业发展的普遍特征。因此,清代前期这些地区的社会重建主要面临的是荒地无人承种、本户与佃户县际互换而形成“世佃”等问题。因而改革的重点也围绕世佃入籍与里甲合理摊派进行。以上皆表明了清代前期北方贫瘠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特征。本文以山西吕梁山区石楼县为例,对其清代前期荒地问题的形成与地方社会的应对进行分析,以此考察其间产生的区域社会结构变动过程。
一、清初的荒地除豁与里甲归并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山西地区产生了大量荒地。荒地的出现造成了原额的损失,但为满足军费支出,稳定财政来源,顺治初年山西虽有除豁荒地钱粮之请,但未能获准,仍主要采取荒熟并征的田赋征收政策。荒熟并征造成的结果是荒地钱粮实际上成为空额,“熟者犹完,荒者仍欠,拥此纸上之金钱无裨实济,徒滋吏胥之索求,反为混淆,是荒者不能完,而熟者又为荒累矣”。尤其是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荒熟并征也极易造成“穷民莫支,转而为盗、为寇,党羽辈未必不由饥困所迫而附合之也”。据此,顺治四年(1647)巡抚祝世昌到任后,着手对全省地进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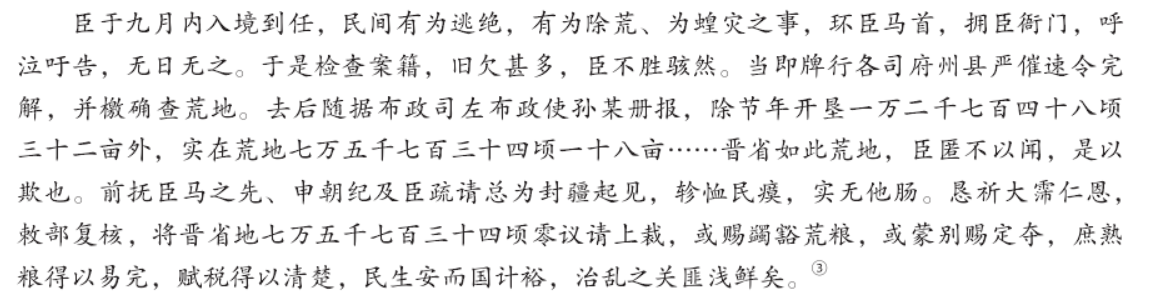
当时共上报75734余顷荒地。按照清初荒地蠲免制度,一般将荒地分为有主和无主两种,直接进行豁免的荒地主要是指无主荒地,而有主荒地主要采取停征优免政策。因此,祝世昌并未申请对全部荒地进行豁免,而是请求或蠲豁荒粮,或采取其他方法。根据顺治十三年山西巡抚白如梅的追溯,顺治四年题请豁免的七万余顷荒地中,有主荒地32200余顷,采取免其三年以前钱粮的措施。因此,顺治四年实际上豁免了43534余顷无主荒地。石楼县的荒地除豁即在此过程中形成。
石楼县地处山西西部吕梁山区,与陕西省清涧县隔黄河相望。按照雍正《石楼县志》的描
述,其地“围绕皆山,既无平土,又无河渠,无田可耕,无井可凿。民间地亩尽在高岗斜坡之
间,即雨旸时,若收获止得邻封之半。不然潦则直流而下,旱则如炙而稿。兼且时令太迟,他处桃李实而石始华,他处禾黍秀而石始播。刮暴风于盛夏,陨肃霜于新秋,万物向荣之候,一宵露结萎靡。地薄且确,不宜禾黍,仅栽杂粟,藉此供赋租不敷粮矣”。以上描述大致表明了石楼县面临的地势不平、旱涝频发以及地处高寒时令太迟等问题。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石楼县是山西最为贫苦的地区之一。
此外,地处黄河沿岸与陕西省交界的区位条件也对石楼县造成影响。例如,明末曾在此设守备把总,以防“水贼乘间窃发”。崇祯五年(1632)李自成从石楼县东渡黄河,据城四十日,造成了人逃地荒的残破景象。因此,明代末年起石楼县就面临着“一遇歉岁,不南走于秦豫,即北窜于边疆。丁粮无着多,至现丁代亡丁,熟地代荒地,包赔累户,俱不堪问”。顺治二年(1645),石楼县曾“奉文踏勘”荒地,但未能准豁。在顺治四年山西全省性的荒地除豁中,石楼县最终除豁无主荒地1944.595顷。石楼县原额民田共地2759.915顷,除豁以后仅有实在熟地815.32顷,除豁荒地额占土地原额70.5%。此后,顺治六年石楼县又被陕西叛将黄进禄攻陷,造成了新一轮的人逃地荒。但可能因顺治四年荒地除豁力度较大,此后石楼县再无荒地上报。相较而言,其他一些与石楼县邻近地区的荒地除豁却几经波折。例如,永宁州和吉州直到顺治十三年才最终完成荒地的除豁。可见,石楼县在清初荒地除豁中较为彻底与及时。
荒地除豁的目的是使“熟粮得以易完,赋税得以清楚”,但在除豁的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清初对明末加派进行豁免,但一些地区的加派银实际上并未豁除。尤其是一些荒地除豁后,其加派银仍被保留。石楼县的加增银和站银两项由明代万历时加派。顺治四年荒地除豁后,钱粮虽然免除,但其加增银和站银“仍照原额荒熟起征”。当时荒地加增银764余两,站银375余两,二者按照原额起征造成了“至有丁粮俱绝,而赔累加增驿站者比比在册,由是四年巡抚祝题免荒,荒已除而粮仍在熟”d。到顺治十四年,知县周士章在处理飞洒钱粮案时,才对此进行豁除。
但整体上看,顺治四年的荒地除豁是对明代末年以来石楼县荒地问题的一次彻底调整。荒地的大量除豁促成了里甲赋役体系的变动。里甲体系的形成主要由编审户口而来,但其运行则需依靠土地和人口的结合。清初的人亡地荒造成了里甲的残破,“人丁既少,地土自荒,地土既荒,均徭自缺”。因此,清初大规模豁免荒地亡丁之后,山西多数地区进行了里甲归并。归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直接将里甲裁废;一种是将几个里甲合并为一;还有一种是将残破里甲并入其他里甲。通过里甲归并,地方政府重新建立起荒地亡丁大规模除豁后的赋役征收体系,作为土地和人口恢复之前的临时性调整。
石楼县主要采取第二种归并方式。早在崇祯九年(1636),面对丁逃地荒的局面,石楼知县熊时泰就曾将十二里并为三里。顺治四年除豁荒地亡丁之后,石楼县延续崇祯间的合并里甲原则,将原六坊十二里合并为一坊三里。具体的方法是“并坊为里,并里为甲”,即将原齐礼坊、在庆坊、镇西坊、问津坊、朝阳坊等坊裁并,仅存崇文坊作为里首。然后将荒地亡丁最为严重的石羊里、谭庄里、东庄里、曹村里、交口里、西吴里、崇德里、上辛里、义牒里、留村里等十里合并为一,称为十攒里,各里分别为十攒里内的甲。最终形成四大里,即崇文坊、君子里、上吴里和十攒里。
里甲归并是为解决荒地亡丁造成的赋役难支问题,但此后的恢复过程中,其又是里甲之间赋役不均、代为赔累的根源。因此,最终将各里甲恢复完整,使土地和人口重新结合是社会重建的重要目标。这也是在县志中详列原来各里甲的重要原因。h在这一逻辑下,虽然十个里作为甲合并为一里,但实际上仍保留了原来各里的独立性,此后荒地的垦复及其产生的问题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
二、垦荒进程与世佃问题
荒地除豁的目的是减轻钱粮征收的压力,防止包赔的产生及其可能带来的荒地进一步扩展。但除豁并非目的,在原额主义下,钱粮压力减轻之后即需对荒地进行招垦,然后以一定宽限进行升科,最终使荒地重新进入赋役体系。但在像石楼这样的贫瘠地区,荒地的报垦升科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是招垦的困难,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员为考成而进行的捏报垦荒;一方面是已报垦荒地与熟地之间的钱粮不均。这使垦荒进程中荒地问题不断重现。
在鼓励垦荒的政策下,石楼县的荒地报垦始于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八年共开垦民田下等荒山地386.5868顷。此后,康熙元年(1662)至三年又开垦原蠲免无主民田额内下等荒山地121.72顷。康熙十六年清出隐漏无主旧荒额内民田下等山地100.795顷。经过以上几次报垦,到雍正时期石楼县共开垦荒地609.1018顷,实在熟地1424.4218顷,但此时仍有原蠲未垦荒地1335.4932余顷,荒地复垦额仅及顺治四年蠲免荒地额的三分之一。
垦荒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劳动力的缺乏。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石楼县因地处山陕交界的军事要地,“石之父子相吊,莫不轻去其乡,以此地为畏途”。由此造成的人口亡失在入清以后很难迅速恢复。同时,又有大量劳动力为躲避差徭而逃往其他地方,“土著之民规避差徭,逃遁他邑者比比皆是”。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也缺乏对垦民的吸引力,尤其是一些原额土地实际上根本不堪耕种。清代土地原额基本以万历清丈为依据。石楼县在万历清丈中将许多实际上不可开垦的土地清丈入册,造成清初除豁的荒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季捏报的老荒地。从雍正时期知县袁学谟对荒地情况的分析来看,“原蠲未垦荒地一千三百三十五顷四十九亩三分二厘,俱坐落深山绝顶。周围三四十余里杳渺无村,尽是榛荆蔓草,狼虎蛇虫出入无常,以致人迹不到。即间有临涧平川,亦为乱石涌塞。此地之八十余年民当富庶,值三次报垦所以断不能垦复者,由来固已久矣”。而一些土地的开垦受到自然环境变动的影响,有很大的偶然性。例如,县西三十里的团圆山附近本无水源,顺治九年五月间山半坡涌出清泉,刘家舍窠、米家岭和白家山等地藉此以灌溉,因而“三庄荒地俱熟,粮无赔累,里人记异”。
由此可见荒地复垦之不易。因此在垦荒政策的压力下,石楼县出现了捏报开垦的情况。顺治十二年,由于当时地方胥吏谎称地亩九熟一荒,知县杨某不得不勒报开荒地亩共计367.4815顷。对荒地实际未垦地区来说,捏报势必造成熟地的赔累。因此勒报开垦造成了恐慌,“各里愚民互相传说,惊诧难支,人人思逃,不复安土”。
对于已经报垦升科的荒地,升科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弊病。例如,顺治十三年钱粮造报后,经过两个月的催征劝谕,各里甲仍输纳困难。知县周士章在该年四月到任后未接到前任移交的文册,以为该地地处山区,较为残破,故办纳不前。但在预造顺治十四年易知由单时,周士章发现“赤历所载额征钱粮总数无差,惟后填各甲细数户同地同,而纳粮折色、加增站银多寡悬绝”。经调查,这些输纳不均是由于里书温玉成和刘成龙任意飞洒钱粮,造成各户里甲“大粮折色、加增站银,成熟开荒派编不一”。周士章通过对比顺治六年赤历册发现,顺治七年曾有加派城工,但布政司采取的措施是以地丁合算粮石人丁进行加派,并无地粮增加。而温玉成则将成熟地亩私自改增为815.32顷,较顺治六年多开地14.605顷。顺治八年又私增粮数,较顺治六年多开1569余石。此后数年,赤历册多开地粮同前,但实际仍按照私增以前折银之数进行征收。顺治八年后,城工加派已经豁除,但里书上下其手,对“已加之粮不行豁除,入册之地不行开粮”,将钱粮任意飞洒,形成户甲钱粮不均。此外,明末加派的加增银和站银也“仍照原额荒熟起征”。
在对以上问题的调查中,垦复荒地折银与熟地存在很大差别的问题凸显出来,即所谓“熟地粮多而银少,荒地粮少而银多”。按照易知由单,熟地仅折银每石六钱多,而顺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开报的四十余顷荒坡地每石折银竟至一两六分。由于里书的飞洒摊派,开垦荒地钱粮比熟地负担更重,这便阻碍了此后荒地的进一步开垦,因此知县周士章感叹到“将来荒地尚有何人开垦”。
可见,顺治年间石楼县不仅荒地复垦有限,还产生了荒地加增站银未除、复垦荒地折银较重以及捏报开垦等问题。顺治十三年到十五年,周士章对此进行了调整。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对开垦荒地折银较重问题,他申请顺治十四年易知由单及赤历册仍照赋役原额改正均平。其次,周士章认为荒地夏秋粮银既已除豁,加增银和站银二项也应“相应照荒熟折算,一并除豁,其原额不敷,俟招劝开垦,荒亡额尽,而加站原额亦可复矣”。第三,对捏报垦荒地,一方面“随传阖邑绅衿里老,委曲开导,百计招留,出示晓谕,不遗余力”,然后让各里派遣本里生员,“给以脚力,前往抚劝”,以消除人们的恐慌情绪,避免逃亡的发生;另一方面,经过临县知县及刑科的勘验,确定勒报开荒地亩系难以耕种的石田,实际上并未垦种,最终在顺治十五年得以豁免。
以上诸项问题的产生与周士章进行的调整显示了顺治年间石楼地区垦荒进程的缓滞。周士章关于召集流亡的论述,表明了当时招垦的主要来源与面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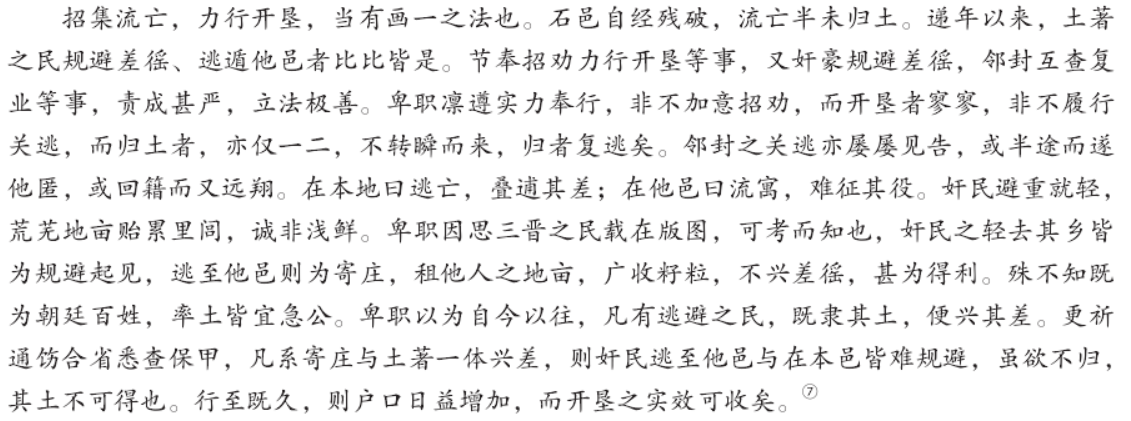
垦荒的主要来源是对流亡的招抚。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土地贫瘠地区,招抚的目标主要是逃往相邻地区规避差徭的逃户。但既已成逃户,虽力行招劝仍是归土者寥寥,且不稳定性极高,很容易产生复逃现象。由此民户“轻去其乡”是石楼这样的吕梁山地的重要社会特征。周士章以石楼县为本位对本地地主逃亡、流寓、寄庄等现象进行了描述,据此提出严查保甲之法,希望全省通盘考虑。从“邻封互查复业等事”可以看出,民户逃亡并非单向度的发生。相反的动向也出现在相邻地区,即其他地方逃避差徭赋役的民户也在石楼县定居,形成寄庄、流寓。这些民户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相沿数代后形成世佃,又称“迷失人氏”。雍正时期世佃已成钱粮征收一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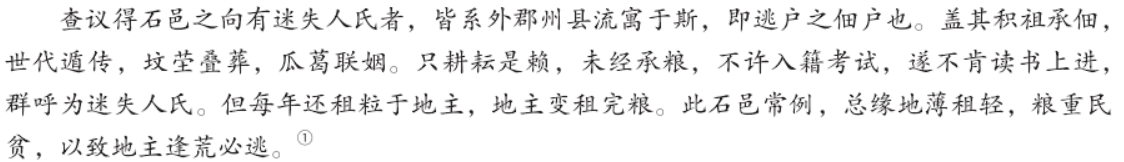
根据时任知县袁学谟的调查,当时“各佃承种地亩,相传数世,结亲葬坟,均有四五辈不等”。由此推算,雍正时大量世佃当在清初垦荒过程中迁入。其中以崇文、上吴、西吴、曹村四里世佃居多。还有一些佃户自明代末年已经迁入,相沿十世。从来源上看,石楼县世佃多来自邻近州县,尤以隰州最多。而逃亡则远者“不南走于秦豫,即北窜于边疆”,近者主要迁往邻近州县,如大宁、汾阳、孝义等地。
通过周士章和袁学谟对逃户和世佃描述的对比,可以发现清代前期石楼县土地垦种的完整图景。除去明末已经形成的佃种方式,招抚流亡进行垦种过程中,地主或由于差徭负担或受灾害影响极易形成“归者复逃”,由此“佃户出租,地主纳粮”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荒地开垦模式。被称为“迷失人氏”的佃户放弃了合法占有土地和参加科考等权利,在石楼县定居。而石楼县的地主也以相同的过程在其他地方成为“迷失人氏”。借助这种方式,地主得以逃脱差徭,佃户则只纳地租。逃亡地主的钱粮一般由同里之人代管,这样虽可以租抵粮,但“同里代管逃户之粮,即代收逃户之租,其中全不致侵婪入己,然亦不无预支挪垫之弊”。可见,这种地主与佃户的分离,造成了复垦荒地极易成为赋役摊派的对象,形成了上述荒地负担较熟地为重等问题。由此循环,又可能产生佃户逃亡、土地复荒的情况。
这种现象在吕梁山地普遍发生。例如,在汾西县也出现乱后荒地由流寓租种,并产生诸多弊病。在光绪《汾西县志》中,风俗一条描述了这种荒地垦种模式:“汾土广人稀,乱荒后全赖流寓租种。刁诈里排故欠己粮,混推租户,拖欠勒加数倍,流寓裹足,地荒粮欠。”这种县际之间互换的佃种模式对旨在恢复原额的垦荒进程造成严重影响,也使里甲体系的恢复更加困难。
三、康雍时期的调整与社会结构变动
康熙年间,石楼县又面临新一轮的荒地问题。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年与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年吕梁山区分别出现的两次大灾,造成了新的人逃地荒。为了维持里甲体系,荒地产生后一般由该户同族或同里同甲进行补种,荒地钱粮也由补种者承担。若荒地无法开垦或无人承佃,赔粮则由理应补种的同族或同里甲进行代赔。同族、同甲、同里的摊派也由此形成。这种应对措施反映了清代国家应对荒地问题的一般态度,即认为抛荒土地一般易于开垦,如果放弃钱粮则易造成报垦升科的拖延,对国家财政不利。因此,一般是进行赋税减免以后,以开征促进荒地的方式尽快垦辟。这在清初荒地除豁中,地方官员与户部对有主荒地是否进行除豁的分歧中也有明显体现。但实际上,这些被认为易于复垦的荒地也经常无法及时补种。在此情况下,根据就近原则进行的代赔成为地方应对荒地问题的经常措施。为了防止摊派超出里甲,形成更大范围的赔累,一般禁止跨越里甲的摊派。例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一书中收有《编审条约》一文,作者沈骏声曾于康熙十八年任临汾知县,为在编审过程中避免陋习,故订立条约“通晓合邑粮户并书胥人等”遵守。其中对飞荒问题严令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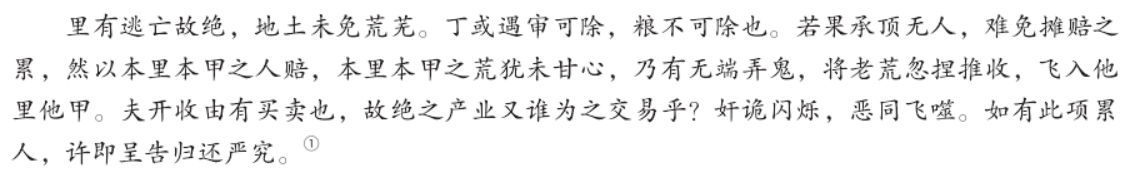
其中提到了缺失丁粮二者在编审中的差别,“丁或遇审可除,粮不可除也”。这是由于人口的亡失一般不可再查考,但由于地荒形成的缺粮却因土地仍在,不能免除。然而,在荒地数量较大地区,里甲残破根本无法负担赔累钱粮,里甲之间的摊赔遂成为地方官员应对荒地钱粮缺失的重要方式。随着荒地的垦复,摊派钱粮如何归还原里甲或进行重新分配也成为地方必须面临的问题。
康熙十一、十二年间因灾歉造成土地荒芜后,为解决荒地钱粮征收问题,石楼知县任玥将十攒里六甲(原西吴里)的无着荒地钱粮100余两拨于崇文、曹村、上辛、义牒等四殷实之里分帮垫赔。为了维持里甲体系,按当时“里倒归里”成例,仅将无着钱粮分派四里,而因灾形成的荒地仍归西吴里管业,以此为权宜之计。此后,西吴里得以复业后,分帮钱粮理应拨回由西吴里继续承担,但“历任因循,该里蹉跎”,代赔钱粮仍由其他四里赔纳,造成“彼盈我缩,偏苦不均”。康熙末年的灾害使康熙十一年、十二年后形成的里甲摊派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灾后曾代赔西吴荒地钱粮的上辛、义牒等地也有荒粮不能完纳。据此,上辛、义牒等里要求将分帮荒地钱粮拨回西吴里承办。到雍正时,袁学谟初定将西吴里有余租100两补上辛里30两,剩下70两抵补全县逃亡无着之项。但是,此时西吴虽已复业,如果将100两全部拨还西吴,又可能造成西吴里的地荒人逃。因此,经过袁学谟调剂,由上辛里拨还24两,义牒拨还16两,崇文坊拨还8两,曹村拨还2两,也就是说仅将其中50两拨还西吴,以减轻西吴里的负担。
康熙末年大灾之后的荒地问题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针对灾后荒地钱粮无着问题,知县梁在韩及后任麦士伟为顾及考成,将无着钱粮垫解完公。麦士伟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其他地方童生代完荒粮30两即可入籍石楼参加考试。此例一开,有24名外县童生以此方式入籍石楼应试入学,共获捐银700余两。但当时石楼县仅有八名之定额,且外县以此方式入籍者“俱系能文之手”,因此捐银之例对本地士子科考形成很大影响,可能造成本地士子的逃亡。通过各种挪垫,最终钱粮得以完解。但垫解完公造成的影响之一是长余民欠的产生。所谓长余民欠系“晋省康熙五十八九六十等年年岁欠收,州县钱粮征比不前。恐碍奏考,挪垫以足分数。后有升迁事,故民欠未及征完,致有此长余”。后由于有所恢复,麦士伟又对稍有复业者进行征收,以补实在无着钱粮。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在里甲难支的情况下“移新完旧,勉强赔补”。由此形成钱粮“垫而征、征而赔”的弊病,到雍正初年已经无法完解。
雍正五年(1727)以后石楼县钱粮已是“积欠累累,不下万有三千”。具体来看,“累年逋欠积至一万一千余两,又加五十九、六十、六十一三年带征,继又被前任麦令报出长余民欠数千两实不能追外,又麦令私征隐匿银一千五百余两,牛种银三百两”。为解决长期积欠问题,袁学谟采取一系列方式进行补足。雍正八年的钱粮最终由民户上缴的牛、马、骡、米、菜、豆、麦等货物折银交官完成。雍正六年共积欠银830两,袁学谟以夏秋二季养廉银共补足400两,其余430两也由民户进行抵补,“查看各户抵算货物细数一纸,其胪列者与前相同,更有木柜、瓦瓮、女儿未受之财礼、牲口未产之胎驹,零零星星,愈奇愈琐,要皆官估垫于前,而民指偿于后者也”。雍正七年和雍正五年钱粮内分别有无着银800两与700两,七年800两内以春季养廉银抵赔200两,余下600两,五年700两内以夏季养廉银抵赔200两,余下500两。d余下的1100两袁学谟劝谕佃户抵补地主所欠钱粮,并鼓励已完粮者,“将次年租银多寡预支一二”。其方法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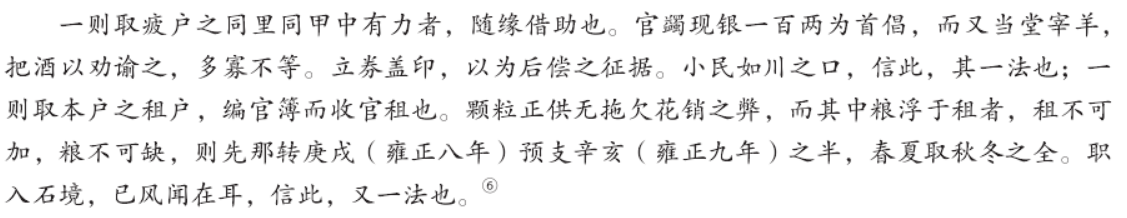
两项措施是袁学谟到任两年多后,把握地方社会特征的结果。“卑职历任两载余,深悉地方利弊。查种地之人,俱系外县佃户完租,奈租不敷粮,其土著所留花户地主寥寥无几。内有殷实者,设法完粮,其疲累者拖欠节年数百十两不等,又有将租银花费积欠,终无底止。”前一项措施改变了以往硬为摊派的方式,而是鼓励劝谕,将赔粮由一部分当地有力者承担,避免摊派造成的贫户逃亡。第二项措施针对地主与租户分离造成的征收困难,以官租的方式直接向租户征收钱粮,并以预支的方式进行补齐。通过上述方式,袁学谟最终将雍正五年到雍正八年的新旧钱粮全数征解。对于贫瘠的石楼地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也引起了对其挪移的猜疑。经过汾州府的复查,确定其中各项钱粮并无挪掩情弊,袁学谟受到了巡抚及布政司的嘉奖,“纪功以示鼓励”。
将清出租银编为官租的方式反映了在劝谕抵补积欠钱粮的过程中,租户、佃户实际上已经成为承担无着钱粮的重要来源。在其他州县也有类似的调整。例如,在康熙十五年(1676),隰州即将上留里由于人逃地荒造成的钱粮缺额,设法编为官租以便输纳,作为权宜之计。这体现了佃户带来的钱粮征收困难在吕梁山地的普遍情形。以官租的方式进行征收,使佃户承担钱粮,跳过本户或代管钱粮之户,“不使贫民拈手”。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本户和佃户分离带来的钱粮无着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佃户仅完地租而不纳钱粮的弊病在康熙末年灾害后的凸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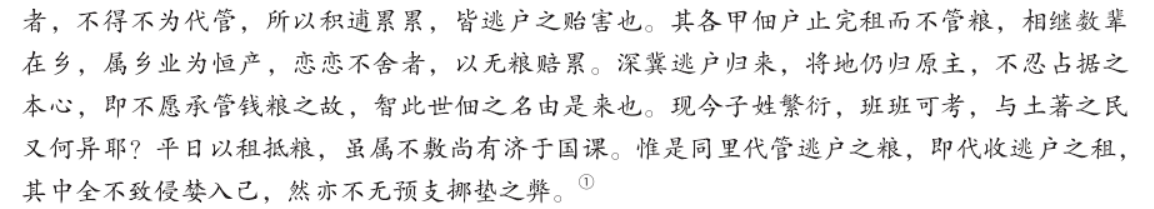
可见,世佃对地方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人众则霸占多方,户富则择买肥产”,久踞石楼却不承担相应丁差地粮,“胆敢狡诈多端,勾引棍徒,相冒合户,托言隰州现有丁差,故意脱漏石邑户口”。相反,石楼本地逃户在他地已经承丁,而在石楼丁银仍由本地土著包赔。由此形成了世佃与土著之间的赋役差别,“一值年荒赋缺,其寄籍者数世子孙居然无恙,而土著之孑遗辗转流离,利则归己,害则贻人”。因此,在雍正七年四月,袁学谟着手进行世佃入籍的改革。具体方法是,“将前项绝户所遗地亩劝谕各佃承粮,请照开垦例印给执照,准其永远管业。所有各佃子孙一体考试,从此佃有恒产,野无旷土”。同时将佃户编审承丁。
与将租户编为官租不同,世佃入籍更进一步确立了佃户对土地的占有权与参加本地考试的权力,与土著一样纳粮承丁。但到雍正八年世佃入籍仍未完成。其原因是“世佃因见旧粮未完,诚恐累及于身,未免逡巡观望”。对此,袁学谟进一步晓谕各佃户旧粮已清。对于“投具亲供者数十余家”,按照佃户“所种之亩分,定其应完之粮数,或逃亡一户之土地,尽属世佃一家之版图,肥瘠均予照粮定额,丝毫不得增减,便成恒产而不出价”。同时颁发印信执照,将逃户之名擦除,以佃户之名顶补,以防原地主与世佃之间的纠纷。
世佃入籍承丁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形成的佃垦模式较为彻底的改革。这从制度上将垦荒中形成的佃户纳入石楼县,为里甲体系的恢复提供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稳定佃户,防止土著逃脱,袁学谟还分别采取了禁止地主混争佃户开垦成熟地,停止冒籍入试等措施。
从康熙年间到雍正时期的调整,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处理荒地问题上的务实化倾向。最终袁学谟的措施基本解决了石楼县的钱粮积欠问题,但此时仍有大量荒地未能开垦。一方面是清初除豁荒地的复垦有限,原额无法恢复;另一方面是灾害造成的新荒地。雍正初年,全国范围内进行报垦清查隐漏,而当时石楼县面临的荒地情形是,“其东南与隰州、孝义交界处所,虽系土山层叠,远近尚有村墟,约计熟多于荒;其西北以及沿河一带,土坡荆棘居民鲜少,约计荒多于熟矣;至若团圆山、漫塘坪、白家岭、黄云山有五六七十里之长,一二十里之阔,崇山峻岭,人踪杳无,是仅有荒而无熟也”。在报垦压力下,袁学谟申明原蠲荒地中的未垦荒地大多捏报于明朝,俱系不堪垦种者,而无隐垦地亩,并奏请仍照顺治四年除豁之例进行免除。
此后,问题便集中到康熙末年灾害形成的新荒地上。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等三年灾害后,石楼县因灾歉形成新荒地计419余顷,经垦复后仍有280余顷未垦。到雍正年间,新荒地每年赔纳徭银400余两,粮银1700余两,形成“以荒地而纳熟地之粮,以熟地而包荒地之课”。袁学谟认为,若将新荒地钱粮抛弃,地亩荒芜最终势必仍造成赔累,而将其钱粮按照此前方法进行摊派则会造成民户苦累。因此根本的办法仍是进行招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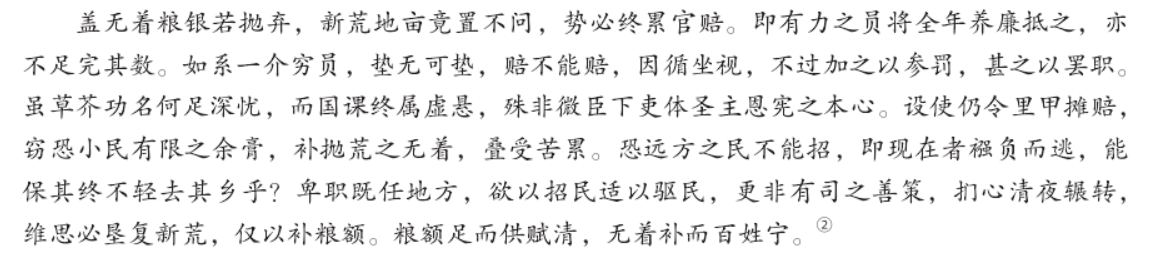
据此,袁学谟组织了对新荒地的查勘。调查发现,除崇文坊、君子里两地人口稠密,很快便垦复新荒地七十余顷“稍济无着”外,其他新荒地仍主要集中在清初荒地较多的十攒里。这些新荒地未被开垦的原因与其所处区位有关,即较之已垦复者离村庄较远。但这些荒地“究属内境”,与不可开垦的老荒地情况不同,“尚有旧窑可修,新穴可开,附近居民可以分栖,可以管摄”。
招垦的具体措施是,按照原蠲老荒开垦之例,借公银以做开垦之资,将未垦新荒地分为三股:以雍正九年开垦111.47顷为一股,雍正十年50顷为一股,雍正十一年50顷为一股。先拨1600两借予九年开垦,于该年秋收后还726.8两,以此作为十年各户开垦之资。余下873.2两由其垦户在十年秋收后全数归还。在其归还银中拨720.4两作为十一年各户开垦之资,余下152.8两起解。而十年所借公银在该年秋后先交一半,剩下一半在十年全数交齐,十一年开垦所借公银在该年秋后交一半,余下在次年交还。与此配合,招垦之地将作为永业颁发印信给佃种各户,并严禁原主待荒地开垦成熟之后混争复业。根据袁学谟的上报,雍正九年春“履庄计亩,亲加督劝,约开新荒地一百余顷”。

但部分新荒地的复垦仍面临很大问题。例如,十攒里二甲即原谭庄里皆山坡陡地,“阖邑穷苦逃亡,未有如谭庄之甚也”。谭庄原各甲绝户土地因无子孙或子孙逃亡,无人代管钱粮从袁学谟的呈文来看,当时应有由生监代管钱粮。但生监未逃者只有一甲、二甲、五甲和十甲,其他六、七、九三甲无人代管。因此,虽拨给籽粒进行招垦,但仍有“地荒粮重,每年不能清新粮,积年不能完旧欠者”。上文提到,袁学谟曾用养廉银代为赔垫积欠钱粮,但此非长久之计,以生监代管也非善全之策。对此,袁学谟将谭庄荒地直接分给其他里甲,以其经管耕种,抵补赔粮。
雍正十年三月,袁学谟召集全县各里到城隍庙,将谭庄各甲荒地钱粮以抓阄的方式分给其他各里。崇文坊拈得谭庄四甲粮49余两,君子里拈得谭庄二甲粮38余两,上吴里拈得谭庄三甲粮61余两,十攒里一甲原名石羊拈得谭庄一甲粮71余两,十攒里四甲原名曹村拈得谭庄五甲粮34余两,十攒里六甲原名西吴拈得谭庄七甲粮50余两,十攒里七甲原名崇德拈得谭庄十甲粮61余两,十攒里八甲原名上辛拈得谭庄六甲粮43余两,十攒里九甲原名义牒拈得谭庄九甲粮42余两。其地粮九里照户均分到殷实甲户名下,地价照户照亩均认,每粮一两出价一两卖予各里作为永业,以达到“众姓承粮,则粮担可轻”的目的。d所得地价用以偿还此前新荒地开垦中借予谭庄的牛种银。
通过这一方式,谭庄里无力垦种的荒地得以有人专责开垦,荒地钱粮固定到特定甲户。如果说康熙十二年西吴村荒地粮拨给其他四里分帮时,仍秉持“里不出里”的成例,土地仍留本里,雍正年间的谭庄分派名义上是荒地卖为永业,实际上打破了“甲不出甲,户不出户”的成例,直接将荒地及其钱粮分给其他里甲进行开垦承粮。与直接摊派相比,拈阄的方式一方面确立了不同里甲之间的摊派差别,而非不分等则进行硬派,另一方面以荒地卖予摊赔里甲的方式将荒地与摊赔里甲直接联系在一起,形成摊派者开垦荒地的压力。因资料欠缺,具体的实施效果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见的是,其他里甲拈阄所得荒地若距离较远,必不能自己耕种,若无人承佃,实际上便是对谭庄荒地钱粮的赔垫,不同之处是这些荒地卖予拈得里甲为永业。
袁学谟也意识到出卖荒地给其他里进行专责开垦可能存在的风险。虽在呈文中表明荒地承买由各里甲情愿甘结,毫无强派逼勒情弊,“各里民人俱皆乐从,舆情允协”。但出价一两作为买价,除了防止产权上可能产生的矛盾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拈得荒地者“视他人之产上紧经管,子孙仍欲退还本里”,其中也可见将荒地作为永业卖予其他殷实里甲的赔纳实质。
在康雍时期的垦荒与熟而复荒的变动中,石楼县清初以来的荒地问题不仅未能解决,反而日趋严重。地方官员为考成起见进行的赔垫、摊派等措施多是权宜之计,经过长期积累,到雍正时期,赔垫、摊派等方式已经再无法解决荒地带来的钱粮无着问题。袁学谟以养廉银和民户征集进行抵补赔垫,完清旧粮以后,逐渐抓住了垦荒进程中本户和佃户县际之间互换这一问题。从而进行了世佃入籍的调整,并对新荒地继续进行招垦,进一步明晰新荒地的责任者。在这一过程中,垦荒佃户通过纳粮承丁进入赋役体系,无人耕种的荒地也被确定到具体民户下进行管业。由此,在制度和事实上形成了新的土地和人口的结合。
四、结语
清代前期的社会重建一定程度上是在垦荒进程中得以完成。然而,垦荒进程并非线性的发展。在战乱、灾害与赋役负担下,土地熟而复荒、荒而复熟以及部分荒地的持续存在是土地贫瘠地区的常态。荒地问题也在此情况下具有层累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在清代前期鼓励垦荒的政策下,石楼县的荒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灾害和赋役负担的影响愈演愈烈。由此,民户“轻去其乡”成为石楼县这样的山区社会的显著特征。不过“轻去其乡”似乎只是问题的表面。由于区域内不同地方存在相似问题,在政府垦荒压力下,本户和佃户进行的县际互换成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垦种模式。在这种策略性的退出机制下,地主藉此得以逃脱差役钱粮负担,而佃户则只需完租,在地方社会中也放弃了合法占有土地与入籍考试等权利,被称为“迷失人氏”。由此相沿数代,形成世佃问题。本户与佃户互换的垦种模式造成了荒地复垦进程缓慢、荒熟钱粮不均及无着钱粮扩大等问题。同时,在灾害的影响下,这种脆弱的人口和土地的结合极易被打破,又形成新的荒地问题。这些积弊最终在雍正时期集中爆发,使钱粮征收面临巨大困难。石楼知县袁学谟围绕世佃入籍、新荒地招垦以及里甲之间合理摊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清初以来的荒地问题及其带来的钱粮积弊最终得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长期聚居石楼县的垦荒佃户被重新纳入版籍,得以纳粮承丁,并给予参加科考的权利。里甲之间的荒地赔粮摊派也在不断调整中趋于合理,进一步稳固了里甲体系。这些措施最终在制度和事实上形成了石楼县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结合。
刘志伟的研究指出,“由于合法占有土地和参加科举考试,是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下两个最重要的上升途径,而这两种资格都必须以户籍为根据,所以户籍成为把‘编户齐民’与‘无籍之徒’、‘化外之民’之间社会身份区分固定下来的制度性因素”。以往关于土地开发的研究中,土地基本上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合法占垦入籍似乎是人们的一种天然诉求。例如,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和黄河滩地开发等相关讨论中,人们围绕土地资源进行了各种纷争、权利划分以及文化建构。谢湜对清代前期南中国的研究,也揭示了地方政府务实化的管理趋势与民间占垦合法化策略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结构过程。但问题的关键是,民间土地占有的合法化诉求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吕梁山区的例子表明,一些地区土地本身的贫瘠状况造成了人们以土地为累的策略性退出。例如石楼县的“迷失人氏”显然同时放弃了合法占有土地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这种情况下,社会重建缺乏动力,以致地方政府因循旧有国家制度框架,以国家力量的介入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
大致同时,康熙时期广东、福建等地的“粮户归宗”改革触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在吕梁山区,与里甲内部户族结合的趋势不同,民户“轻去其乡”的社会特征形成了一种社会离散的趋势。荒地问题造成的代管和代赔等问题,使户族和里甲内部结合困难,更多的是逃绝而形成的户族和里甲的分散。户族内“子孙俱靡有孑遗,无人经管”,同里甲代管之人“因粮累逃走,忽往忽来”,这是户族和里甲内部面对荒地问题的常态。而县际之间地主和佃户的互换,以及里甲之间的摊赔,使人口与土地极易分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地方政府对此进行调整的主要目标是稳固旧有里甲体系,重新确立人口和土地的结合,使里甲人户承担相应的钱粮差役。即使久踞本地的世佃在出现蒙混合户的倾向想要逃避赋役时,也被世佃入籍的改革切断,以纳粮承丁的方式被重新整合到区域社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