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托克维尔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 7454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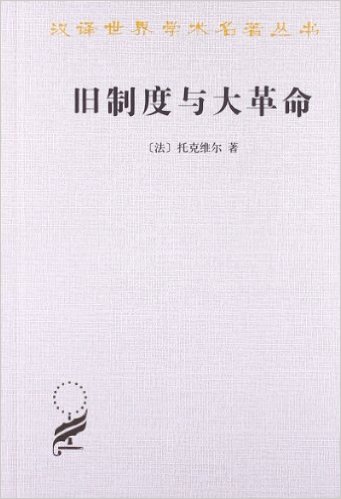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1849年10月被路易·拿破仑解职。他也因反对1851年12月的路易·拿破仑政变而一度入狱。
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本书推荐
改革与革命的迷思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王岐山
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任 明
【摘 要】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还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成为法国构建自由宪政道路上的隐秘障碍。他主张法国从美国经验中汲取智慧,培育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团体以对抗政府权力集中化的倾向。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央集权
托克维尔的文字总是透露出其对历史和时代的洞幽察微与清醒判断。作为托克维尔最有力员最为成熟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却被傅勒称为“引用的人多,读它的入少;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1]。其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多将注意力投向书中无处不在的妙语警旬,未能整全地看到他从历史坟墓中复活的旧制度及其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真知灼见。笔者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主旨在于阐明路易十四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导致大革命的爆发,还朔造了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成为法国构建自由宪政道路上的隐秘障碍。走出旧制度的阴影有赖千在法国既有的中央集权与单子式个人之间建设有活力的社会中间团体,而这需要从美国经验中汲取智慧。
一、旧制度与中央集权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对中央集权存有误解。他们只看到了大革命将以往一切推翻在地的激进性,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新事物。通过对18世纪法国历史文献的研究,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产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2]。
托克维尔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法国在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被中央淹没,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贵族远离权力中心,各地区、各团体的政治自由逐步丧失,中央政府儿乎实现了对国家全面而绝对的控制。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还不在千其强大的压迫性,而是其无处不在,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进入国民的日常生活。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3]中央集权下的政府已担当起社会“监护人”的角色。
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托克维尔认为这既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演进的结果,也渗透着以魁奈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的思想。他们普遍注重行政权力,轻视政治自由,反对针对政府权力建立任何制衡力量。经济学派勾勒出的理想社会正是大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在旧制度下这个社会已隐约可见。
二、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法国
托克维尔从几个方面描述了旧制度下的法国。
第一,贵族制度名存实亡。从路易十四开始,国王逐步任用平民出任行政官员,贵族不再是掌权阶级,沦落为只享有身份特权的封闭的种姓。他们把居住地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此与土地失去了直接联系,同农民的关系也从领导者蜕变为收取地租的债权者。贵族原本是中央政权与农民间的纽带与屏障,但失去权力并离开农村使贵族彻底摆脱了对农民的治理义务,也导致农村共同体因缺乏领袖而难以凝聚,直接暴露在中央政权之下。
第二,司法独立浪灭。中世纪的法官由贵族出任并终身任职,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国王控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路易十四以后,国家行政机构的司法权力不断扩展。御前会议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多,司法机构所制定的条例在“大革命前40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部分不经御前会议裁决修改”[4]。御前会议还以“调案”的方式“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5],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最终将与行政有关的所有诉讼从法院系统中剥离出来。
第三,地方自治湮灭,中央控制地方行政。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克服封建制度的多样性,控制地方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甚至“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砃塌的墙垣,必须获有御前会议的裁决”[6]。大革命前,中央行政权力已经逐步侵吞了城市与农村的自主与独立。而一旦地方自治被剥夺,地方权力被抽空,人民也就只能听任强大的国家权力为所欲为。
第四,旧制度下的法国人相似并疏离,形成一个原子化社会。中央集权制摧毁了具有自由堡垒作用的社会中间架构。一方面,所有人都处于同等地位,变得极为相似,”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7];另一方面,人们彼此疏离,难以合作,“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8]。就这样,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当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权力时,由于缺乏中间团体的保护,只能任由国家侵害。
第五,人民缺少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的机会。牧人式中央集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民政治生活的丧失,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萎缩。托克维尔对此深有感触:"尽管知识已普遍进步,可是离我们年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倒变得模糊、杂乱无章、记载不全而且混乱不堪。[9]贵族和资产阶级被集权政府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整个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民众因失去了自主管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变得对中央集权尤比依赖,“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0]。他们处处求助于中央政府,以至于在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11]。因此,一方面,中央集权消解了社会力拭,另一方面,分散软弱的社会力橇又强化了中央集权。可以说,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及其对国民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的剥夺,已在各方面为旧制度的毁灭和大革命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三、新法国的旧制度阴影
推翻君主制、建立新法国的大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其“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12],因为革命之后的国家本质上是旧制度及其精神的延续甚至加强。旧制度已削弱了封建制,大革命则完成了它未竞的事业;旧制度包含中央集权,大革命则强化了中央集权。新旧法国在很多方面惊人地相似,新政权中处处可以看到旧制度的影子。
第一,法国大革命以激进的方式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 ,但旧制度的核心 中央集权制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新社会得以巩固。表面上,大革命攻击一切现存权力和传统习俗,但“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13]。这是因为大革命进一步打碎了社会的中间团体,革命后的社会由孤立的个体组成,面个体又是虚弱的,不足以胜任公共行动,于是中央集权成为构建国家的基础。这一历史逻辑曾由信条派领袖人物、被托克维尔视为精神之父的罗亚·科拉尔做过精当阐释:“革命留下的只是个体……化为废墟的社会之上出现了集权……事实上,在只有个人的地方,所有不属于个人的事务都是公共事务,是国家的事务。”[14]
第二,旧制度塑造了法国的民情,而民情不仅作用于大革命,也对法国未来产生潜在却不可忽视的影响。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15]。革命者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方案再造一切。法兰西民族对中央政府的信赖,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门,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16]这种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在19世纪始终是法国民情的一部分,它不是肇始千大革命,而是深藏于旧制度。
第三,在新法国,已被旧制度启动的社会原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个人主义社会逐渐形成,政治让位于私人生活,政府集权化更加明显。旧制度和大革命共同摧毁了保护个体的中间组织,弱小的个体倾向于退回私人世界,远离公共领域,个人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的信念。人们醉心于物质福利,把公共利益弃置一旁,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这样,一方面,社会中间团体被打碎,个体只能仰仗集权政府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对财富和安逸的追求使人们不愿献出精力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强大的政府帮助他们谋求福利。而令托克维尔忧惧的是,在这个单调划一的大众社会,当个体退居于私人生活而陷于孤立时,专制将乘虚而入。
旧制度摧毁了社会中保障自由的中间团体,塑造了具有集权倾向的民情,而革命后的新法国,人们在追逐私人享乐中彼此疏远,逐渐丧失单独或相互合作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能力,转而一致性地依赖行政权力,其结果就是“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17]。就这样,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后的新社会得以重生,并从此成为法国政治的一条主线。托克维尔写作此书时大革命已结束六十多年,背负着集权重辄的法国却仍步履踉珊地在革命与专制中挣扎,看不见自由的踪影。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法国,只有一件事情办不到,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坏不了的制度,则是中央集权制。”[18]
四、托克维尔的药方:向美国学习
只有走出旧制度的梦魔,才能破解法国的历史难题。面对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人与高高在上的全能政府,如何建立自由宪政?这始终是托克维尔思考与写作的现实关怀。同时代的很多法国人都把英国模式视为榜样,认为英国才是法国的未来:“1789完成了1640,现在的法国所期待的是在将来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实现1688。”[19]对此,托克维尔并不认同。
为什么不是英国?托克维尔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会对其政治选择做出限定。英法革命发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有很大不同,英国宪政秩序的建立有其独特逻辑。首先,英国的宪政之路是一个渐进过程,贵族作为政权的建设性力量存在,政府处在持续的调适中;而法国已经失去了可以保守的政治资源,贵族制度不复存在,也无法恢复。其次,英国革命只是改变政体的政治革命,远未触动社会的结构、习俗和习惯;而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成为一场整体的革命,在“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20]。此外,“在英国,第三等级与贵族联合击败了王权,在法国则是第三等级和王权结盟摧毁了封建制度和贵族”[21],其结果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当然,法国也不是没有任何机会走上英国之路,但终究在旧制度下化作泡影。托克维尔遗憾地写道,法国曾经拥有和英国一样的贵族制度、一样的司法独立、一样的自治传统和一样的自由精神,但路易十四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令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品格,摧毁了社会中间团体,塑造了认同专制的民情,这一切使法国与英国渐行渐远。
既然历史趋势不可阻挡,既然社会结构已成定局,法国就不可能在一个封建制度荡然无存的原子化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包含诸多传统因素残痕的英国式自由宪政,而只能把目光投向不曾经历过旧制度的美国。事实上,托克维尔1831年的美国之行正是在为法国寻找出路。他曾说过,《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主要是为法国人写的……是从法国人的角度写的”[22]。美国经验所展示的正是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如何立国才能避免集权与专制。
对比法国,考察美国,托克维尔主张挖掘和培植社会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专制的因素来构建自由宪政秩序。他重点从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和乡镇自治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重要保障。美国人普遍认为“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23]。此外,构筑社会的公共空间,培植多种社会权力来制约政府权力是保障自由的重要手段。既然法国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天然的社会中间力量,那么结社就是弱小个体联合起来对抗专制、捍卫自由的重要手段。托克维尔还强调,个人只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完全实现自由,因为个体只有走出私人空间,与其他公民一起参与政治,才能克服孤立、软弱而获得力量。美国的乡镇自治更被托克维尔大力推崇。在他看来,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24]。在美国,相对收缩的政府和强大的公民社会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模式,而这正是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原因所在。
从《论美国的民主》到《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作内容不同,背后主旨却一以贯之。托克维尔根据对美国的考察,提出了以培育社会中间团体、促进人民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来保障自由、抗衡行政集权、走出旧制度阴影的宪政建设路径。这是他对法国的思考,而与法国有着相似背景且仍在探索出路的中国未尝不能从中汲取某些智慧,因为“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25]。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页。
[2][3][4][5][6][7][8][9][10][11][12][13][15][16][17][20][23][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30-31、81、93、90、34、3 5、56、107、109、29、48、29、107、32、42、188、104页。
[14][21][22]《思想与社会》编委会《: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19、109页。
[18]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 4年版,第2 17页。
[19 J Francois Furet,"lntellectual Origins of Tocqueville's Thought,The Tocqueville Review(1986),p.120.[2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蜇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