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研究网
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瞿同祖 发布时间:2017-11-29
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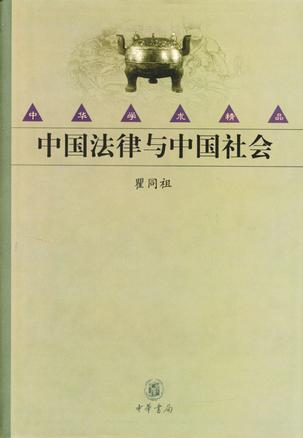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法律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本书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是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作者简介
瞿同祖(1910-2008),长沙人。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年赴美国,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后去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5年回国,历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湖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出席第二十七届欧洲汉学会议。1985年,以高级学者名义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阐述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著有《中国封建社会》、《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
目录
第一章 家族
第二章 婚姻
第三章 阶级
第四章 阶级(续)
第五章 巫术与宗教
第六章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
结论
附录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瞿同祖先生学术年表
社会史视野中的法律瞿同祖访谈
瞿同祖谈治学之道
家庭与阶级: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张 珺
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它结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法律制度,拓宽了研究视野,把“法律之内”拓展到“法律之外”,强调了法律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关系。
本书围绕着“家族”与“阶级”这两大中国传统法律核心概念,阐明了法律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身份等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义务是与其身份等级有关系的,并且同法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瞿同祖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皆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以及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其身份社会是以伦常纲纪作为标准的。身份的区分,是以家族为核心,并且以家族为起点。此外,本书“先家族、后社会”的这种论述方式也可以表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起点和根本所在就是家族主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是整个社会最为基层的政治和法律组织,是构成这一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单位。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父祖在家族中处于首脑的地位,家族内部成员的权利都集中于他们的手中,[1]经济权、法律权乃至家族内部成员的生命权利都由父祖所支配。[2]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性特征体现在祖先崇拜,是家族存在的重要依据以及活动的核心内容,婚姻不过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以及祖先的祭祀。[3]祖先崇拜不仅可以保持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而且家长权也会因家族祭祀的身份而更加神圣化,进而更为强大和坚固。如果每一个家族内部都能维持其家族秩序而对国家负责,那么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自然就能够得到保证。
为了阐明法律是如何在家族社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瞿同祖先生在书中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性进而得到最终的结论。他通过对不同朝代的实例考证,分析了在多种角度下法律在家族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
首先,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赋予父祖以相当大范围的特权,例如惩戒权,它是行使父权的重要方式。在子孙有不孝的表现时,父母可以“呈送发遣”(即请求衙门代为惩罚子女),而衙门此时也不会过多追问缘由,只要具备不孝和父母呈送这两个条件的,都可以进行“发遣”。即便遇到皇帝“大赦”等特殊情况,要是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申请将子女领回,他们也不得被释放。并且瞿同祖先生还要求注意法律及法律机构在这类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律机构即衙门是法律的践行者,子孙要是有不孝的表现,如违反教令或供养有缺,依照法律的规定不过是“杖一百”,如果是同样的过失,要是被父母“呈送”的话便要发遣边地,终身不得自由。可以看出,对子女的处分的尺度伸缩实质上完全是由父母来操纵的。而衙门只是代为执行父母的意志,代为行使父母的惩戒权。财产权也是其他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禁止子孙私自拥有财产是儒家礼法上一直存在的要求,即使买卖契约已经成立,其效力也不被法律所承认。家长在世而“别籍异财”更是作为不孝罪名之一。子女同时子女典质或出卖于人,可见家长所享有的财产权有多么大了。
其次,家族伦理也是维持家族精神的一种支撑力量。它层次清晰分明,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表现在定罪量刑是以家族伦理为依据的。不仅体现在家族伦理对父权主宰家族的认可,也体现在长幼之间、尊亲与卑亲之间以及对长者和尊者的伦理性倾斜。[4]对于卑幼犯尊长,若有侵犯的事实,不管动机是什么,关系越为亲近的,处刑就会越重,反之不仅是关系越亲处刑就会越轻,还会着重考虑尊长的主观动机,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此外,由于儒家“礼”的要求,对于亲属相奸等这种乱伦行为的处罚是极为严重的,对其制裁也不会分长幼尊卑,对双方的处分是完全相同的。而对于亲属之间的盗窃等行为,关系越亲则处罚越轻。这些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法律是维护家族伦理和家族秩序的。
最后,完全以家庭为中心的婚姻是家族社会的保障。婚姻的目的是维护宗族的延续和祖先的祭祀,而与婚姻双方当事人没有必然的关系。婚配嫁娶也是父权的一种表现,子女对婚姻没有决定的权利,只可以服从。家长则成为婚姻在法律上成立的要件,如果婚姻存在违律的事由,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并不承担法律责任,而是与直系的尊亲属主婚人有关系。而所谓的“七出”等充满家族伦理性的解除婚姻关系的事由也是为法律所许可的,这体现着家族伦理对传统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以及法律对家族伦理的支持与维护。
“阶级”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核心,瞿同祖先生通过“阶级”这个特定的概念来阐述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社会阶级关系虽然不如家族关系那么复杂,但其身份制度却是同样的严格。按照瞿同祖先生的观点,社会阶层或阶级可以分为贵族官吏、良民和贱民三种。在划分方法上,他强调的主要是社会成员身份的不同,以及各种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所收到的待遇不同,也即“礼”对待不同阶级的人所具有的差异性在传统法律和社会上的体现。这种身份差异在社会和法律上的体现,是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影响。瞿同祖先生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法律对不同阶级的饮食、衣饰、房舍等生活方式,以及婚姻、丧葬、祭祀的规格也是家长的财产之一,家长实际上是子女的所有者,他可以将所作的详尽的规定,每个阶级只能使用法律所规定本阶级使用的物品或者规格,下不得兼上、兼上即违法。在婚姻中,最初的严格的阶级内婚制虽然由于门第观念的逐渐减弱而减弱,但是良民仍是被禁止与贱民通婚的。同时由于阶级的不同,其婚姻缔结和仪式上也存在巨大的反差。
贵族官吏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法律上是享有特权的,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例如他们可以不受拘系刑讯,并且享有议请、依例减赎、官当等特权。非特权的阶级不享有特权,并且在参与诉讼时,法律对于不同的阶级其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特权的人侵害平民、贱民时处罚采取减轻主义,相反则采取加重主义,减轻和加重的程度根据受害人的官阶和地位的高低来决定。因此,官职不仅仅是一个职位,更是“一种身份,一种特权,罢官所失去的只是某种官位的行使职权,身份权利则属于个人而永远不会丧失,除非有重大过失而被革职”。[5]此外,法律也对良民和贱民进行区别对待。法律明确规定贱民的社会地位不同于良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并且不能与良民通婚。如有违反,不仅要对违反的贱民进行处罚,还要否认这种婚姻的效力,并予以撤销。
事实上,“身份制”的调控范围之大,连法律制度,甚至是社会整体都包含在内。可见,社会生活里规定的差异性与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自然发生的差异性逐渐发展成社会的习俗,进而被纳入“礼”的范畴内,并通过教育、伦理、道德、风俗和社会惩戒来加以维护和限制。然后将这些规定编入法典,成为了法律。法律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种体现,其深受儒家礼教的支配。儒家思想在两千年里漫长的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而能达到如此高度,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的,也就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争锋和融合,即瞿同祖先生所称的“法律儒家化”的过程。瞿同祖先生认为:“自儒家化的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编舞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家族和阶级方面是如此。换言之,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他们代表了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亦即古人所说的纲常名教。”[6]所以可以这么说,“法律儒家化”这一过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最大的变革,它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个案判例,通过对这些具体个案分析,来阐明法律的基本精神,又通过家族和阶级关系来说明了法律作出此种规定的原因即“以社会去阐明法律,以法律去阐明社会”。[7]这个评价正是形象地总结了本书的写作特点即并不是只研究法律是怎样对某一问题作具体规定的,而是考察法律在实践操作中是怎么样被运用的,如何生效以及如何对社会、对人民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的。瞿同祖先生社会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使他用社会学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传统法律,采用了法史学和法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突破了原有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传统模式的禁锢,对历史现象进行层次分明的梳理,对大量历史案例进行分析,同时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精准的剖析,这就将两种研究方法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本书的另一个写作范式的特点就是文献的大量运用,不光是正式的法律文献的考证,如《唐律疏议》、《宋刑统》、《明律例》、《清律例》,还运用了判例、野史等,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如《二申野史》、《南部新书》,这些资料丰富,加强了论证的可信度。所以说瞿同祖先生采用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启发我们思考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范式的创新,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析并重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我们来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每次细读都应该有更深的认识,值得我们再三研读、借鉴。
注释:
[1]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页。
[2]同上,第27页。
[3]同上,第6页。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3-402页。
[5]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5页。
[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0页。
[7]胡旭晟:《擦亮二十世纪中国法史学的丰碑》,载《中西法律传统》,中南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