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研究网
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发布时间:2016-12-11
信息来源:中农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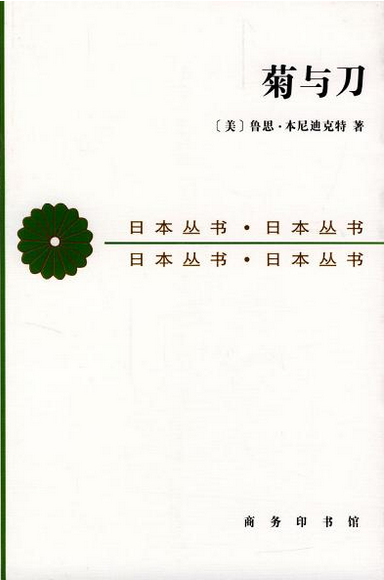
内容简介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目录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明治维新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洗刷污名
第九章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和《菊与刀》
刘毅 关丹
【摘 要】二战后期,美国政府为了制定对日政策,邀请了一批专家研究日本,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格,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作者将研究成果以“菊与刀”为书名出版。书中概括出了典型的日本国民性特征:“等级制度观念”、“耻辱感文化”。
【关键词】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女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在凡萨尔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学期间选修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教授的课程,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出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教授,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学者。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开创人之一,代表作《文化模式》被公认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菊与刀》是她另一部主要著作。
一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依然在欧洲和亚洲大地的上空弥漫。但与此同时,战事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利于法西斯诸国。在欧洲战场,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亚洲战场,日军虽仍在负隅顽抗,但经过中途岛海战,其整体实力遭到重创。1944年6月美军完全占领了冲绳岛,进占日本本土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基于这种局面,1942年8月,美国的外交部门开始为战后占领日本作调查研究方面的准备工作,即在战争结束的前三年就开始为打败日本占领日本做准备。在大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研究,主要在国务院和陆、海军部中进行。为准备战后政策,1942年8月23日在国务院特别调查科之下成立了东亚政策研究小组。该小组“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和平重新到来时,应该考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1]此外,陆军部和海军部也在大战期间积极准备制定占领政策。为了将各方分别准备的政策方案统一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组成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三边调整委员会。1945年1月建立了其所属机关远东小委员会。从1945年1月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远东小委员会开过33次会议,广泛地研究了很多重要的对日政策提案。
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问题。此时,美军正在太平洋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岛屿登陆作战中与日军短兵相接。美国政府对于盟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深山老林中与那些可怕的顽抗分子战斗到底、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是否能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日本投降、战胜日本后是否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是否保留日本天皇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美国政府要求本尼迪克特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情报收集,尽早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以便以最小的牺牲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来讲,本尼迪克特接受的研究使命的确是困难重重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此之前,她的研究课题从未涉猎过日本,本人从也未去过日本,因此,对日本既无感性认识,也无理性认识。更主要的是当时美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无法进行“实地调查”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简直是难以接受和想象的。但本尼迪克特却采取了两种做法予以补救。她和由她领导的研究小组一方面对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及战争中被俘的日本士兵“进行面对面接触”,“询问他们的自身经历,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2]然后用“模式”理论进行定性分析。另一方面是收集、整理所有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材料,既有西方人近百年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也有日本人自己写的著述,从中寻找有价值的材料,用文化人类学家所受的特殊训练,发现那些隐藏在历史文字背后的内容。
1945年本尼迪克特将其研究报告呈交给政府,1946年以“菊与刀”的书名在美国出版。此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已经确定,但是将来美日关系如何发展还未明确。一般的美国人对日本人持有高度的优越感,倾向于继续直接占领,如果美国选择了这种方式,将很有可能引起日本的反美情绪。这样一来不仅会影响到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也有可能因被苏联抢得先机而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菊与刀》的出版表面上是一份对日研究报告的呈现,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对美国的一种特殊期望。期望美国的国民和政府能够正确地认识日本这个民族和国家,阻止那些要对日本提出苛刻要求的人们。
二
《菊与刀》全书共十三个章节,主要内容是由先前的研究报告所组成,个别章节涉及战后的内容是本尼迪克特出版时进行的补充。作者“所预想的读者群应该是美国有文化修养的非专业人士,比如总统、阁僚、议员、财界、产业界的名人、三军将领、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士。”[3]所以书中所使用的语言平易优雅、简明易懂。
十三章的内容着重就日本民族、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伦理道德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而又颇有见地的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对“等级制度观念”和“耻辱感文化”所进行的分析,概括出了典型的日本国民性特征。
本尼迪克特将等级制度观念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各安其分”,从整体上把握日本人的各种思维、行动的模式。主要表现在家庭、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
在家庭里面学习各种礼节是日本人形成等级制度观念的开端。从婴幼儿儿阶段开始,就会教授如何尊敬父兄之类的各种礼节。鞠躬是最常见的日常行为表现,在家庭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妻对夫、子对父、弟对兄都要鞠躬,女孩子更是对弟弟哥哥都要鞠躬。鞠躬除了外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等级制度观念。鞠躬者承认受礼者对自己的行为的干预权,受礼者承担自身相应的责任。日本人对家庭观念的重视也能反映出等级的色彩。父亲在家庭拥有特权,比如在洗澡的时候具有优先权,长子作为继承者在家庭中几乎与父亲拥有同样的特权。拥有特权的同时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维系家庭。本尼迪克特认为,“建立在性别、辈分、长子身份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人们在家庭中对等级制思想进行学习,并“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应用到经济和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领域”。[5]
在社会生活中,日本人的等级制度观念表现得更为充分。在交往中,人们每一个行为都必须表现出彼此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往时要明确彼此的等级关系,并使用严格恰当的敬语,同时还要配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即使在同一等级内,还要考虑年龄、性别、家庭关系和双方以前的关系。
在国际交往中,日本人也同样持有等级制度观念。二战期间,日本试图在国际等级中谋求上级,希望亚洲在其领导下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在世界上希望与欧美列强一同居于等级秩序的顶端。日本人将国内的等级制度观念转移到了国际社会交往中,在“共荣圈”的问题上,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比作弟弟,自己为兄长,对弟弟的事情强加干涉,充分体现出了日本家庭中的“兄长观念”。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应该统一于一个固定的等级制度之中,各国各族人民应该“各安其位”。
“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赋予日本文化的“人格类型”,是对日本人行为模式的总概括。书中作者将“耻感文化”与欧美社会的“罪感文化”进行了比较。罪感文化源自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原罪论。原罪论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而并非完美。因此,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忏悔和悔悟之心。在这种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对人的善恶进行审判。本尼迪克特认为,“一个社会,制定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且依赖于人们良心的培育,这种社会文化是‘罪感文化’”。[6]因此,只有在罪感文化中生活的人才有向上帝进行忏悔的行为。
耻感文化更加强调外在的约束力。自己犯了罪错,并且被发现,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自己才会感到耻辱。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来自社会的压力。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他人排斥为自己的耻辱。“在以耻为主要约束力的文化中,人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但却不能像消除罪感那样,通过忏悔和赎罪而得到解脱”。[7]
本尼迪克特并没有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文化模式作出孰优孰劣的评价,而是认为两者各具特点。两种模式在形成过程和外在表现上存在差异。罪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涉及人与宗教的关系,而耻感文化则是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
三
《菊与刀》所存在的不足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本尼迪克特没能亲自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加之她不懂日文,对日本历史也欠缺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有时会忽视了历史背景的探讨,造成许多资料分析上的错误,把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忽略了年龄、阶层、职业的区别。这样所概括出的日本国民性特征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也作了一些客观的说明。相对于不足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本身所产生的意义。保留天皇制的建议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也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将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8]“日本人之所以能欣然接受这一政策,确切地说是由于日本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9]这种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这种政策的实施日本人避免了因战败所带来的耻辱感。美国的对日政策制定及其后来产生的效果印证了本尼迪克特的判断,因此,《菊与刀》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桓著.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3:16.
[2][4][5][6][7][8][9]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1:11、81、91、349、349、247、253、465、467.
[3]森贞彦著.《菊与刀》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2.
[作者简介]刘毅(1949-),男,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史和东北亚经济史;关丹(1984-),男,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