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5-20 浏览次数: 11977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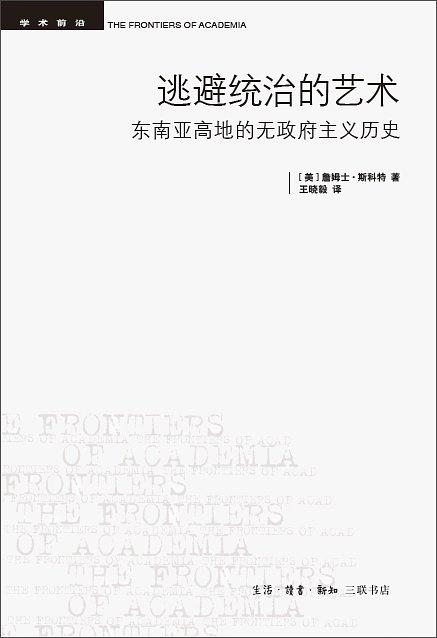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作者简介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20年。
目录
前言
1山地、谷地和国家——关于赞米亚的介绍
2国家空间——统治和征用的区域
3人口和粮食的集中——奴隶制和灌溉水稻
4文明与化外之民
5远离国家,进驻山地
6逃避国家和防御国家
逃离的文化和农业
6.5口述、书写和文本
7族群形成和进化——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案例
8复兴的先知们
9结语
注释
译者后记
“文明不上山”:“赞米亚”人自有的高地生存策略
——读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
谷家荣
【摘 要】“赞米亚”是斯科特打破国家地理边界,基于文化主体主位视角研究东南亚高地人时所借用的概念。斯科特将东南亚高地看作一个超国家空间的文化有机体,结论性地告诉我们:具有逃避特性的东南亚高地文明是国家作用的结果。高地人在自我选择形成的“非国家空间”里,拥有主权国家难以完全控制和操纵的“水母—曼陀罗”式社会结构;他们与低地国家(臣民)保持着有距离的“黑暗双生子”式的经济共生关系;其社会救赎的愿景往往宗教性地渺寄于具有各种神谕性力量的“先知”身上。
【关键词】赞米亚;逃避统治;国家作用
从地方来发现整体社会文明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惯常的研究范式。格尔兹的“深描说”、费孝通的“类型比较说”都堪称经典。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或解剖麻雀式的微型社区研究能科学地接近整体社会文明。在中国,先辈提醒及其学术经典的示范引导使许多志于农村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学人都习惯把自己的研究起点,定位在单位村庄或微型社区多样经验事件的充分发掘上。先辈们尤其是国外汉学家在进行地方性研究时,都始终没有忘记关怀跨国家地理边界的超时空问题。他们尊重人类文明的自然生产逻辑,并通过突破单位国家空间边界来研究宏观文明体系。或许,正是发现这种学术理路的科学性,美国耶鲁大学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才把并接了中国西南、越南、泰国、缅甸、老挝及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地空间视作一个整体的“赞米亚”文明板块。其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便是该研究进路的代表成果。斯科特直接告诉我们,创造“‘赞米亚’概念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在这里,划定区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也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而是基于特定生态规律和结构关系,这些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1](31)。如此,斯科特把区域文明史的书写摆放到文明群体“本己”上,坚信“文明不上山”是国家作用和高地人积极应对的政治选择结果。他的这一立论从心志上敲打了长期以来始终紧缩在国家空间并单纯迎合统治者意志进行问题推理的研究者,启迪人们回到文化主体内生性的文明制造逻辑去认识“他者”。
一、“赞米亚”:作为“非国家空间”的东南亚高地
“赞米亚”(Zomia)是斯科特从荷兰学者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那里借用的概念。斯科特发现,自越南中部高地,向西横跨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一直到印度东北部的高地山区,居住着1亿多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统治的农民。他为了更好地认识那里的人,将该高地空间命名为“赞米亚”。“赞”(Zo)意为遥远,生活在山上;“米”(Mi)意为人民。“赞米”(Zo-mi)指边远的山地人。“东南亚山区实际就是碎裂带。……地理上相对难以进入和非常多样的方言和文化”[1](10),山民“拒绝国家,甘当无国家的民族”[2](297),“选择与低地文明中心及国家保持距离而逃往高地的人,他们的农业、社会结构、文化,甚至可能包括他们的无文字状态,都是这个选择的结果”[3],“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1](2)。因此,斯科特用“赞米亚”这个词来表述处于国家边缘的东南亚大陆山地。
“赞米亚”是东南亚农民的“逃避走廊”,文化复杂多样。在国家空间,为了更好地控制臣民,国家往往通过土地和人口清册及相应的国家机器进行简单统治。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东南亚高地难以奏效。在有巨大地理困难的东南亚“无国家空间”,往往是反抗和逃避统治人群的天堂,国家很难建立和维持权威。这个断裂带像百衲被一样,那些“化外”之民很少强调要有清楚的边界,地理高度可以被赋予原始性。基因、观念和语言的流动与交换密集和多方向,任何企图通过完全清晰的一组地理、语言、生物或历史文化特征来区别和描述不同族群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里根本没有部落这回事,没有客观的宗族、遗传、生物或文化公式可以把一个部族明确地分别开来[1](301)。
“赞米亚”高地农民习惯“自我野蛮化”,常被污名化为逃避统治的“生人”。基于国家文明,人们习惯将原始的都定义为“生的”,那些所谓的高地蛮夷也常被归属到“不文明”群体中去。从国家意义上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生态的密码。那些没有固定居所、经常游动和不可预期的人群被置于文明之外。人们往往认为,固定的水稻耕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山地农业在视角上显得没什么变化,因而山地人被认为与自然接近而抵制文明,将自己保护在国家之外就会被标记为“不文明”。东南亚高地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特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管理。斯科特认为,在东南亚高地,“生”与“熟”的边界划分不能完全依靠文化来权重,应主要看“是否服从汉族的统治”。“熟”和“生”的定义主要是政治的,与文化的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要从行政控制而非文化本身来理解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族群分类的发明[1](142-144)。所谓“生番”就是国家机构强制管辖范围之外的人。在国家眼里,高地的蛮夷是否能被教化是次要的,关键在于能否从他们那里得到税收。那些缴纳税赋的人多生活在国家代理人易于触及的地方,故而被国家视为顺民。山里人不易接近,有些还经营游耕生计,他们是令统治者很头疼的人群,经常被视为逃避课税者,“生”于是成了他们的污名标签。这些避开国家税收人群的行为被视为对国家的“抵抗”[4]。
二、“赞米亚”人“水母—曼陀罗”式的社会结构
水母最大的生理特征是极易裂变和重生。由于东南亚高地人因生计选择而造就的社会结构与水母的生活特性相似,斯科特因此用其来形容东南亚高地人群。他认为,“社会结构不应该被看作特定社区的持久社会特点,而应看作一个变量,其目的之一是调整与周边权力区域的关系”[1](254)。通常,“族群开始于统治和税负停止的地方”[1](145),因为居住在国家便意味着赋税、征募、徭役及被奴役,负担沉重,臣民便会立即迁移到边陲地区。“边陲地带像一个没有开发的稳定平衡装置,国家越是压榨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越少。”[1](5)正是如此,埃德蒙·利奇在研究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时才坚信,“真正有意义的是内在的结构模式,而非外在的文化模式”[5](29)。他对缅甸克钦人“贡劳”“贡萨”制度的研究,正是从其内在的结构逻辑方面给予关注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深入研究孟加拉湾东部安达曼人的社会组织结构时,也同样从岛民的内生本有的结构特征加以研究。他发现,在英国人占领这些岛屿和当地社会组织受到人口下降影响前,安达曼人以小群体的形式分散生活在各岛上,大部分生活在海滨,但也有一些生活在内陆的森林里。每个群体都是独立、自治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处理自己的事务,每个群体与邻近群体之间偶尔联系,“哪怕相隔不到50英里,也没有直接的联系”[6](17)。从久远的历史来看,“赞米亚”是那些为逃避统治而自愿选择和形成的区域。东南亚的一些小国像人力捕获机器一样,不断地把逃避的人口“吐出”到山地,渐渐制造出“野蛮”的内陆边疆。这些地方拥有共同产权的资源(草原、狩猎场和可能的游耕地),为保护和适应这个“非国家空间”,高地人往往兼有采集、游耕、狩猎、贸易、畜牧业以及定居农业等多种混合生计策略。正像水母一样,他们既可以快速地“解体”,也可以快速地“重组”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水母部落’式的裂变使潜在的统治者必须面对一个无组织、无结构的人群,没有一个可以进入或者起到支撑作用的点”,“对于那些无政府的‘水母’似的部落进行稳定和间接的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甚至平定他们也都是困难且短暂的”[1](256,260),“国家的统治者几乎无法实施对于这样一些人的统治,他们总是处于移动中,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地址,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他们很少有稳定的联盟,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民族认同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这些人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都是为了逃避被统合到国家结构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适应”[1](47)。对于高地人来讲,“这种不明确的多重性和彼此间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政治资源”[1](301)。这种极具水母式生命机理的社会结构能给高地人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而他们始终把这种“不确定性”作为最重要的生存资本。
“赞米亚”人的社会结构还具有关系互嵌的“曼陀罗式”特性。斯科特研究发现,东南亚高地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小国,但国家中心都不能完全独占所有高地,高地人分别属于相互竞争的此消彼长的小国政权中心的一员。为了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述这种“国家中心多元化”现象,斯科特借用藏传佛教梵文词汇“曼陀罗”(国王们的圈子)来加以表述。在广泛的“赞米亚”,小国统治者常声称自己有神圣的血统,他们的宫廷基本都建在水稻生产的平原地区,小国的影响向周边传播,从而形成同心圆式的国家空间。但多个小国的国家空间经常会出现重叠,在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地方相互发生作用,于是便出现多个同心圆交叉的“曼陀罗式”社会格局。在这个权力多元的社会系统中,主权拥有惊人的复杂性。斯科特甚至把小国区域假想为平底锅烙出的一张饼,但这张饼并不能始终保证其完整性,沼泽和崎岖山地常会把它切碎成多种不规则的小块,并经由通航的河道而任意将其拉伸。在这些地方,“国家性本身就是循环和可逆的”[1](9)。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多国权力的交叉地,应对高地人无数的策略性选择成为小国政治的重要内容。
“赞米亚”人的“水母—曼陀罗”式社会结构特性是国家作用的结果。东南亚高地那些有意将自己放到国家边陲的“自我野蛮化”文明,多是文明主体精心设计以阻止被统合进国家的一种政治作为。他们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了逃避已有的国家和预防可能出现的国家,是国家作用的结果,是“有意的野蛮”。在高地,“部落是在与其他部落和国家的对话和竞争中人为建构的,是一个政治项目,而不是自然存在的”[1](321),“部落和族群的产生也许可以被称为无国家人民与国家打交道过程中提出诉求的通行方式”[1](326),“是国家造就了部落而不是部落建立了国家”[1](318),“他们的农业实践、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治理结构、他们的传说和他们的文化组织,都带着逃避国家或远离国家实践的痕迹”[1](153),“他们远不是被谷地文明进步所‘遗弃’,而是经过长时间努力,自我选择了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外”[1](26)。“山地的社会结构和居住方式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政治选择”[1](37),“我们应将山地社会解释为社会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包括他们的地点、他们的居住方式、他们的农业技术、他们的亲属实践,以及他们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被设计来将他们自己置于与谷地国家以及其他周边山地人群相对立的位置上”[1](217),“从任何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国家权力边缘的地点必须被看作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不是文化和生态本身固有的”[1](222)。放大区域空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毗邻地区的高地人群具有相同的文化模式。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研究发现,那里的帕坦人通常以裂变和复制的方式组织起来,没有集中化的机构。他们的父系继嗣、伊斯兰教及风俗习俗都极具本土性特征。这种“本土模式”提供给帕坦人一种自我形象,并作为衡量由他本人与其他帕坦人所表现出来的普遍行为标准。如果这种本土模式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自我形象,并能恰当地与在社会交往中所经历的某些认知相一致的话,它才可以被保持下来[7](104-107)。在斯科特看来,“部落之所以经常看起来是稳定、持久、具有谱系和文化一致性的单元,其原因之一是国家往往希望它们这样,并且在长时间中逐渐将他们塑造成这样”[1](255)。总之,高地人的这些行为选择都是在与国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国家和高地人共同“打理”的结果。
三、“赞米亚”人“黑暗双生”的经济共生关系
“赞米亚”高地人与谷地国家(臣民)之间存在经济共生关系。作为国家的破碎区域或边缘地带,高地人“不让国家文明上山”,始终坚守和逃避在“非国家空间”,但他们与谷地国家及其臣民之间始终保持距离。“他们所逃避的并非是与国家发生关系,而是逃避处于臣民的地位”[1](412),“生活在山地的人们无法离开平地居民”[4],“谷地国家与山地人相互构成了对方的影子,既是互惠的,也是共存”[1](34)。高地人与谷地国家是合作关系,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谷地国家作用下的“黑暗双生子”。这个较具反讽的共生差序在高地农民和低地臣民的农业种植以及日常经济生活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高地人有能力、有条件种植水稻,但他们并没有,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选择。高地人的刀耕火种、游耕,甚至在不同的耕种方式中变来变去的做法都是国家权力的反应,我们永远不能说游耕更原始,它其实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其目的是远离国家[2](296)。为了适应这种农耕方式,山地人还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和祭祀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这些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1](10)。
高地人与谷地国家(臣民)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利互惠的经济交往。卡尔·G.伊西科维齐研究发现,在老挝,“寮人和其他的泰族人控制了湄公河上的贸易。来自山里的每条支流流入湄公河的地方,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那里有庞大的寮人村落。他们选择这个位置是为了给山地部落提供贸易上的便利。在这些村落里当地产品被聚集在一起,然后再用皮筏和独木舟沿着湄公河转运出去。山地部落的产品由虫漆、藤条、蜂蜡、西班牙胡椒粉、大米、小豆蔻等构成。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森林居民的刀和铁质工具。他们也购买罐子、寮人的布匹等等”[8](124)。亨宁·西弗茨在关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高地的族群时发现,那里的人口表现出异源性特征。那里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社会,它以构成单位之间的经济专门化和共生的相互依性为基础[9](101)。事实上,“谷地的政治实体,特别是小政权都被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严重依赖山地贸易,对他们来说。山地贸易伙伴的背叛是一个严重威胁”[1](127),“尽管谷地国家可能从山地捕获奴隶,但他们需要保障他们所依赖的山地贸易生态区位不会没有人”[1](129)。其实,“大多数的高地人都曾经是低地人,他们逃向高海拔地区,开始了精密而复杂的分化过程。在其新的生态环境中,各种不同的逃亡民族采取了新的生存规律”[1](163)。同样,作为一个整体,东南亚的谷地国家也被居于山地、沼泽、迷宫般复杂水路中的相对自由的社区所包围,这些社区也同时代表了威胁、“野蛮的地方”、诱惑、避难所和贵重物品[1](221)。所有东南亚古典国家都会想象出,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山地、林区和沼泽中有一个野蛮的内陆,他们既需要蛮夷边疆,又需要吸收和改变边疆[1](131)。因此,斯科特明确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有关抵制国家的空间研究不仅仅要包括山地,而且需要把低湿的地方包括进来,包括各种沼泽和湿地,以及荒野、三角洲、红树林海岸和复杂水路及群岛”[1](205-206)。只有坚守这样的学术进路,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东南亚高地社会独具特色的山地文明。
“赞米亚”人“黑暗双生”的经济共生关系是国家作用的结果。高地人在与谷地国家,包括殖民政权的许多世纪的持续“对话”中,许多策略被制定并细化出来。在许多重要方面,这个“对话”是由山地社会和水稻国家共同构成的,双方都代表了不同的可选择的生存、社会组织和权力模式,任何一方都在复杂的模仿和否定关系中“追随”另一方。山地社会在谷地国家的作用下运行。高地人“从事移动农业明显是政治选择。……选择了游耕,或者基于同样的理由选择了采集或游牧,就是选择了停留在国家空间之外。这一选择在历史上为东南亚平民享有自由奠定了基础”[1](233),“从事山地农业就是选择了远离国家框架的政治生活”[1](236)。国家乃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破碎地带,每一方都处于另一方的阴影下,因为有了对方才有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谷地国家的精英是通过与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比较来确定自己作为文明人的地位,同时也依靠他们来进行贸易和增加其臣民的数量。反过来,山地也依赖谷地国家获得重要的贸易物资,他们在距离谷地王国很近的地方利于赚钱和打劫,同时又保持与王国的距离,不让自己在政治上处于直接控制之下[1](407-408)。无论是居住地点还是社会或农业生态结构,高地群体都有很宽广的范围可以进行选择。大多数采集者和游牧民,可能还包括游耕民,都不是原始人的遗留,而是在国家的阴影中所产生的适应的产物[1](417)。“在山地居住人群的文化中看起来已经聚集了大量复杂的技术使他们既可以逃避国家的统合,同时又可以从邻居那里获得经济和文化机会。”[1](409-411)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国家长期存在,高地人与谷地国家(臣民)的共生关系就会长久成为“赞米亚”惯常的现象。
四、“赞米亚”人的社会救赎:渺寄于“先知”的愿景
东南亚高地围绕“先知”的社会动员,既意味着国家的形成,也意味着反叛。“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10](11)“赞米亚”人宗教信仰的社会性特征体现得非常突出。大多数高地人有很长的逃避历史,在面对谷地国家的猎奴、纳贡、军队、瘟疫和不时的作物歉收时,高地人只能采取多变的生活形式与国家周旋。在这种近乎迷宫般的生活世界中,根本不具备任何优势的高地人为了尽可能地寻求生活的确定性,往往将回归“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存救赎宗教性地寄托在那些所谓的“先知”身上。由于被看作神圣的力量且充满魔力,那些“先知”运动很容易披上外来的宗教外衣。“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认同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边界形成机制,意在强化政治和社会差异。”[1](188-195)“没有特权的人不希望保持现有的地位和财富分配,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秩序重组获得利益。他们更加被那些承诺建立全新时代的运动和宗教所吸引。”[1](370)许多“先知”都有一个关键的承诺,就是要纠正不公正以恢复平等地位,甚至将不公正现实彻底翻转。正是在这些一无所有的边缘人群中,那些更加革命、翻天覆地的预言实现了山地人的最大诉求。“先知”们非常强调救赎宗教中的世俗功能,有公正的王或佛陀,有重视并重建公正的神话,有充分的理由憎恨谷地国家。
高地人的各种“先知”共识是国家作用的结果。东南亚高地人的文化认同与谷地国家的关系直接相关。要在强大的谷地国家夹缝中生存,他们必须革新和调整多种生存技能以适应国家,这就不能不使其文化认同也同时标记上非常易于临时建构的特性。在一个口述文化中,不存在某个权威的、作为最标准和最正统的谱系或历史。在存在两个或更多解释的情况下,哪个更可信,主要取决于口述者的立场以及绝大多数听众的利益和口味。所谓的最初概念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以及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的关系,并非表明他们处于进化的低级阶段。”[1](293)当然,“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1](271)。简单通过策略性的选择和强调某些特殊的祖先,高地人可以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真实”谱系以帮助他们表明现在联盟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精心设计的族谱实际上是一组可能的盟友名单,尽管多数还隐藏在阴影下,但一旦需要就可以被召集起来。社会环境越混乱,族群的分裂和重组越频繁,就会有更多被阴影遮蔽的祖先出来起作用[1](288)。其实,东南亚高地“先知”动员的“反叛”不仅逃避和温和地抵抗了谷地国家,而且在高地族群内部也防止了新型国家的产生,进而使得“文明不上山”的“赞米亚”文明维续了相当长的时段。
五、结语
东南亚高地文化持有者的一切文化发明都是在逃避国家统治和适应东南亚高地政治及自然环境中综合权重的结果。高地人的“曼陀罗—水母”式团体格局与国家始终保持距离。从国家本位讲,我们可以把相当一部分“赞米亚”人视为难民,但这相当污名。高地人并非初始就是没国家归属的流民,他们的逃避身份本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文明“上山”,本是为了国家治理的简单化和清晰化,实现大一统意志。要实现这个理想,高地人需要完全拥有主权国家公民身份的平等机会。可遗憾的是,历久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这种最为基本的群体诉求未能得到满足,“赞米亚”人才被迫步走上与国家有距离的逃亡生活。斯科特认为,山地人的历史最好不要被理解为古老过去的残留,而是从谷地国家政权建设中逃亡的历史。当然,也正是这个距离的存在,时时给国家制造不同形式的麻烦。这是统治者根本不容许的,他们积极动用国家机器,试图把逃避人群归属到国家空间。于是,“赞米亚”高地文明被巧妙地造就出来。从这个层面上看,“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和共存的,表面上是对抗的,但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1](28,11,20,3),“如果没有与低地中心的持续对话,我们不可能写出一部条理清楚的山地历史,同样如果忽视了其山地的边陲,也不可能写出条理清楚的低地中心历史”[1](31-32)。事实上,斯科特想告诉我们:东南亚高地人为了逃避国家统治而坚持“文明不上山”,是高地人建构跨时空的“赞米亚”文明的基础逻辑。只是,由于民族国家现代通信技术以及交通枢纽的快速发展,这一文明生产法在二战之后便不再生效了。国家文明上山,赞米亚高地人的文明艺术呈现出更加显明的国家特性。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美]詹姆斯·C.斯科特.文明缘何难上山?[A].王晓毅,渠敬东,编.斯科特与中国乡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1).
[4]范可.论“山地文明”[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5][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导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A].[挪威]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挪威]卡尔·G.伊西科维齐.老挝境内的邻居们[A].[挪威]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墨西哥]亨宁·西弗茨.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A].[挪威]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导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